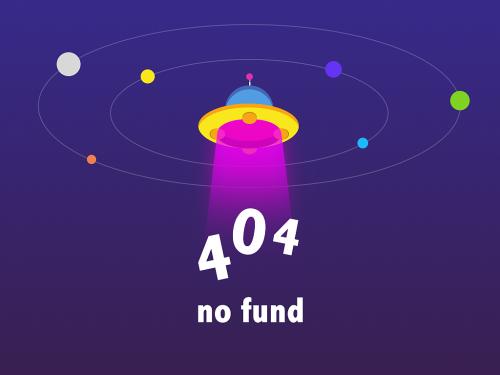
新作《爱历元年》通过婚姻生活勾勒社会世相的变迁、历史小说《大清相国》借历史表达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官场文学”是简单武断的文学命名……17日上午,著名作家、今年鲁迅文学奖得主王跃文出现在南国书香节上,与读者分享他的新作《爱历元年》,以及他对时下文坛、文学现象的一些思考。
新作《爱历元年》通过婚姻生活勾勒社会世相的变迁
王跃文最新长篇小说《爱历元年》,写一对知识分子夫妻,出身平凡,受过高等教育,拥有稳定的工作,事业和生活都处在上升期,却不能免俗地双双出轨。“在生活中,这些故事的结局,往往不是身体上鼻青脸肿,就是心灵上伤痕累累,不是家庭四分五裂,就是亲情分崩离析。”王跃文在小说里却拒绝了这种结局,他让男女主人公在故事的最后,通过内心的抗争获得自我救赎,悄然回归情感的起点,重启“爱历元年”。对结局的处理,体现了王跃文的写作思考:生活其实比小说更颓废,更令人沮丧,但之所以最终选择了温柔和温暖,是想让读者相信,破镜能够重圆。这是一个作家给予这个时代最美好的期许。
熟悉王跃文写作的读者发现一点:无论是写官场也好,乡村也好,还是写中年知识分子的家庭生活也好,他所写的基本都是生活的日常状态,都不是大起大落的故事情节。对此,王跃文说:“我不喜欢故意把故事搞得波澜壮阔,非常曲折,甚至离奇,我觉得那不是生活的常态,而是生活的极端状态;如果文学总是写这种极端状态,未必能够揭示生活的本质。”
《爱历元年》到底想表达什么?王跃文说,他想通过对一对知识分子夫妻的情感婚姻生活轨迹的描摹,对中国人过去二三十年间的精神走向、灵魂沉浮、情感形态等进行回望,同时采用草蛇灰线的手法对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社会世相的种种变迁也作了勾勒。“中国这二三十年走得太快了,各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事情,很多问题,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想清楚,一切该发生和不该发生的,都发生了,让每个人措手不及。”王跃文说,所以,当社会被某些辨识不清的洪流裹挟的时候,当所有人都貌似向前奔跑的时候,他更愿意把自己当成一个低调的观察者,专门关注那些非极端的人情冷暖,“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我想看看那些狂奔的人得到了什么,又丢失了什么,然后真诚地写下他们的故事。”
历史小说《大清相国》借历史表达对现实生活的思考
17日的活动海报中,《爱历元年》被称为王跃文“《大清相国》之后的长篇小说”。很多读者的提问都涉及到《大清相国》的话题。去年,因为一篇热门新闻报道中提到中央领导人曾向下属推荐阅读《大清相国》一书,使得该书迅速洛阳纸贵、售罄断货。《大清相国》是部历史小说,塑造了以陈廷敬为主要代表的大臣群相,反映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和行为的艰难选择,再现三百多年前的官场风云。小说写道,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陈廷敬却驰骋官场五十多年,历任工、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乞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
很多读者好奇地问王跃文:创作题材怎么会由现实主义官场小说转入了历史小说?王跃文则认为,这种转身很正常。“我时而写现实题材,时而写历史题材,时而又写乡村题材,所以经常面对是否创作转型的问题。其实,所谓转型的提法是很偷懒的一种理解。好的作家必须是丰富的,题材的丰富是其重要方面。”王跃文说,“我写作《大清相国》是个例外,因为某种特殊机缘了解到这位古人,并去山西阳城皇城相府的陈廷敬故居作了考察和寻访,研读了大量历史资料。我十分敬重这位先贤,他有学养、有干才、有品格,值得后人敬仰。我写《大清相国》,最主要的目的是向这位先贤致敬。”
《大清相国》除了是对陈廷敬这位古人的敬重之外,也寄托着王跃文对现实生活的一些思考。他说:“我们生活是往前走的,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也不应该回到过去。但是我们对历史不能够采取无视的态度,在历史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我们经常讲借古喻今,还是可以把一些古代好的东西发表出来,所以历史小说也不失为一种方法。”
“官场文学”是简单武断的文学命名
有王跃文在的地方,自然少不了“官场文学”这个话题。对于“官场小说第一人”这样的称呼,王跃文说,他非常不喜欢“官场小说家”和“官场小说第一人”这个狭隘的称呼。“这是媒体贴在我身上的狗皮膏药,想撕也撕不掉。”王跃文不赞成这种简单武断的文学命名,“如果依据这种划分,我可以说《悲惨世界》是犯罪小说,《老人与海》是渔业小说,《红楼梦》是青春小说,《西游记》是玄幻小说。”
对于官场文学的火爆,王跃文分析说,官场文学之所以异常繁荣,原因毕竟是多方面的。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不会变,这就是任何文学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官场文学之所以那么多,正是由于现实土壤的滋养,读者需要它,渴望了解这个领域,它才如此兴旺发达。
对于一些评论家认为官场文学是通俗文学、文学价值不高的说法,王跃文有自己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流派、任何类型的文学现象,放在一个漫长的文学史当中,都只是一个文学史的过渡期。所以当下对官场文学的种种指责,不可以看作是否定官场文学的足够理由。百年之后,当后人回望这段文学史的时候,可能看到的是另外的风景。我们固然可以对官场文学满怀信心或者怀抱敬意,但是丝毫改变不了官场文学在现实社会当中遭遇到的不公待遇。